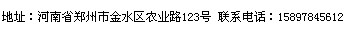射频消融治疗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之我见
目前,国内报道使用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相关文献共5篇。年刘晓岭等[8]首次报道了对9例患者,11个PTMC病灶行RFA治疗。随访时间为12个月~18个月。结果显示:所有患者治疗后恢复顺利,未出现术后并发症。随访期间9例患者消融区域范围均缩小,甲状腺及区域淋巴结未见复发和转移。刘晓岭等[8]认为RFA可用于无淋巴结转移PTMC的初始治疗,并且安全、有效。但RFA治疗后是否存在癌组织及转移淋巴结残留,还有待更长时间的随访。同年刘博[9]对10例患者,12个PTMC病灶行RFA治疗并且认为使用RFA治疗PTMC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年Zhang等[10]在Thyroid杂志报道了RFA治疗92例患者98个低危初始治疗PTMC病灶的治疗情况,治疗后平均随访7.8个月。结果显示:共24个结节彻底消融,在RFA区和残余甲状腺组织中均无肿瘤组织残留或复发,无可疑淋巴结发现。颈部轻微疼痛1例,暂时性声音嘶哑4例。Zhang等[10]认为RFA可有效治疗低危PTMC患者,术后并发症低,可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一种新手段。另外,年还有两篇文献报道使用RFA作为PTMC的初始治疗,两篇文献的结论均认为对PTMC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RFA疗效显著,安全性较好,值得进一步推广[11-12]。
从国外的报道来看,将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文献仅有一篇并且仅纳入由于自身条件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患者。年,Kim等[13]将RFA用于6例因全身麻醉或各种基础疾病手术风险大而拒绝手术的低危小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thyroidcancer,PTC)(最大径1.5cm)患者。术后随访时间为4年。结果提示,肿瘤的平均直径由术前的9.2mm,下降到1.3mm,4例患者结节完全消失,2例患者结节仅有少量残留。所有患者随访过程中均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作者认为RFA治疗对于不能接受手术的低危小PTC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但同时也指出,结节的消失并不能证明肿瘤细胞被完全消灭。由于缺乏长期的观察随访,RFA作为PTMC初始的有效性,目前还不能妄下结论。
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将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报道主要出现在国内。这些文献的结论大都认为,使用RFA治疗PTMC疗效好,安全性高,简单易行,可以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新方法。但是基于我们目前对PTMC生物学行为的认识和临床经验,深入剖析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这种方法存在着若干问题。
2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存在的若干问题2.1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无论是年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还是年中国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都将手术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首选方法,单侧腺叶切除是目前PTMC手术治疗的最小切除范围[14-15]。年韩国甲状腺放射学会专家共识和年意大利甲状腺结节RFA治疗共识也均反对将RFA作为甲状腺癌的初始治疗方法[16-17]。韩国的共识规定患者至少应进行两次独立的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fine-needleaspirationbiopsy,FNAB)和(或)粗针穿刺活检(coreneedlebiopsy,CNB)检查以确定结节为良性。即使FNAB或CNB结果为良性,对于存在超声恶性征象的结节行RFA治疗也应慎重对待,目的是杜绝RFA用于甲状腺癌的初始治疗。其次,从目前国内外发表的用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的文献来看,尚缺乏严格的RFA与手术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比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未建立客观、有效的长期随访疗效评价体系。例如,国内的5篇相关研究中仅有一篇为前瞻性研究,均没有设置对照组,最大样本量为92例,最长的随访的时间仅为18个月。这些研究循证医学证据等级低,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
2.2不符合肿瘤治疗的“无瘤”原则
PTMC只代表肿瘤最大直径≤1.0cm,并不代表是早期癌。部分PTMC患者诊断时即出现气管、喉返神经(recurrentlaryngealnerve,RLN)侵犯,颈部中央区及侧方淋巴结转移甚至远处转移。年田文[18]发表的有关PTMC文献指出:PTMC发生被膜侵犯、腺外侵袭和淋巴结转移的比例最高可达66.1%。其中被膜侵犯和(或)腺外侵袭率9.4%~52.2%,淋巴结转移率6.6%~34.9%,多灶癌发生率39%~42.2%。所以,针对PTMC的原发灶,以局部结节消融为目的的RFA治疗难以确保原发灶清除的彻底性,不符合最小切除范围为腺叶的原则,属复发风险分层高危组。如原发灶邻近甲状腺被膜、RLN、气管等甲状腺周围组织器官,RFA既不能将癌组织尽可能地完全清除,也不能保证RLN、气管等周围组织的安全。对于颈部转移的淋巴结,RFA无法将淋巴结成区域地清扫,只能选择性地消除部分转移淋巴结,这种“摘草莓”式的消融势必会导致转移淋巴结的残留。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PTMC的多灶性特点也增加了肿瘤残留的可能。此外,RFA治疗后无法获得进一步病理诊断来明确是何种病理亚型,对患者的术后治疗和随访方案的制定会有影响。对于术后需要放射性碘治疗的病例,RFA治疗后也无法实施I放射治疗,更无法通过监测术后血清甲状腺球蛋白变化来判断肿瘤复发和转移。所以,RFA用于PTMC初始治疗既不能在术中将肿瘤原发灶及转移病灶完整切除,也不利于患者术后接受I治疗和规范化的随访,不符合肿瘤治疗的“无瘤”原则,势必会增加肿瘤残留和复发的几率。
2.3明显增加再手术的难度
随着年ATA指南对PTMC的手术必要性进行了修改,指南推荐对于没有局部侵犯和转移且没有明确的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证实是具有侵袭生物学行为的PTMC可选择密切观察,而不是立即手术[14]。于是部分医生认为,既然可以对PTMC进行观察,那么对PTMC行RFA治疗就更加无可厚非。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各国指南之所以将密切观察作为部分PTMC治疗策略的选项,是因为已经获得了近20年密切观察临床研究结果的支持,而RFA治疗的长期预后在时间上还远远不够。此外,随访观察并没有破坏甲状腺周围原有的解剖结构和组织形态,为日后手术治疗保留了有利的手术条件。使用RFA治疗PTMC,一旦因原发灶消融不彻底或多灶性导致的肿瘤复发和转移将显著增加再手术的难度和风险。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所带来的问题正在日益凸显。如董文武等[19]报道对5例经外院RFA治疗后病理检查证实为PTC的患者进行了再次手术,术中见甲状腺腺体局部组织水肿明显,与颈前肌等周围组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粘连,层次不清,分离困难。术后病理检查显示5例患者均存在中央区淋巴结转移,其中2例还有颈侧方淋巴结转移。董文武等认为应严格把握RFA适应证,RFA治疗后诊断为PTC的患者,应积极手术治疗并且手术应由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来完成。马奔等[20]也报道收治了2例超声引导下经皮RFA治疗的原发性甲状腺癌患者。术中可见病灶与周围组织粘连,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均证实癌灶残留并伴有颈部淋巴结转移。
2.4容易损伤甲状腺周围的重要组织器官
在治疗肝癌、肾癌中,RFA能量范围需覆盖整个肿瘤边缘甚至建立一个5mm~10mm安全边缘。对于与周围脏器或大血管关系密切的病灶需要严格限制其适应证或采用特殊隔离措施。但是从解剖层面来看,甲状腺的体积与肝、肾相差巨大,周围的RLN、动静脉血管、气管和甲状旁腺等重要组织器官严重制约了该安全边缘的建立。对于原发灶靠近这些组织器官者此问题更为突出。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的“经峡部穿刺movingshot”以及“液体隔离带”技术还不能满意地解决甲状腺后背侧紧邻RLN和RLN入喉处等特殊部位的结节。从目前国内从事RFA的医生来看,主要是超声影像科医生。他们对实体解剖经验几乎是空白,对RLN变异以及在气管食管沟内走行的多样性体会不深。以上原因均可能导致RFA对甲状腺周围重要组织器官损伤的可能性增加。
3RFA作为PTMC初始治疗能在国内开展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和质疑声中,RFA用于PTMC初始治疗在国内还有较大市场?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原因:首先是迫于开展新技术的需要,由于射频消融具有设备成本低,技术易于掌握,操作简便等特点,同时拥有大量患者群体,使得该项技术治疗医院快速上马;其次从患者的角度来说,RFA简单、快速、微创的特点既迎合了PTMC患者想得到尽快治疗的焦虑心理,又满足了他们追求美观的需求,而此时又缺乏正确客观的就医指导;再者,医院创收的心态也可能或多或少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到真正从患者的利益出发,严格把握RFA适应证,不要进行虚假过度宣传,积极引导患者采取正确方式治疗PTMC。
4结语综上所述,使用RFA作为PTMC的初始治疗尚未成熟,缺乏循证医学依据,不符合肿瘤治疗的“无瘤”原则,明显增加再手术的难度,易损伤甲状腺周围的重要组织器官。在权威指南出台之前,笔者反对将RFA作为可手术PTMC的初始治疗,只有当患者不能耐受手术或不愿意接受手术时,可将RFA作为手术之外的另一可选方案。同时,建议临床医生应该严格把握RFA的适应证,引导PTMC患者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SIEGELR,MAJ,ZOUZ,etal.Cancerstatistics,[J].CACancerJClin,,64(1):9-29.
[2]HUGHESDT,HAYMARTMR,MILLERBS,etal.Themost